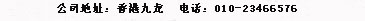聋人不敢购物,有病不敢看病有原因他们无法
聋人观看
请在WiFi下观看视频
医院,他拖了两年没看病周五下午,医院一楼大厅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,他叫范思佐。
范思佐神情紧张焦急,但没有说一句话,只是双手不停地大幅度舞动着。
“他是第一次来看病。”边海桢认真地看着范思佐的每一个手势,同步翻译着,“一年多以前感觉腰部这里痛,现在转移到这里了。”
边海桢是一名手语翻译志愿者,经常来助聋门诊帮聋人看病。范思佐是他这天接待的第一名患者。
边海桢帮范思佐看病
医务人员根据边海桢的描述,将范思佐分诊到泌尿科。在边海桢和一名义工的陪同下,范思佐来到了诊室。边海桢先把范思佐的病情描述翻译给医生,然后把医生的询问内容用手语翻译给范思佐。这样一问一答好几个回合,花费的时间几乎是普通患者的一倍。
“先去做一个B超,要多喝水,憋尿。要憋尿啊,这样才能诊断清楚。”一个基本的常识,边海桢打着手势向范思佐反复强调了好几遍。
范思佐两年前就感到身体不适,但一直拖着没去看病,直到他听说了助聋门诊。他通过边海桢的翻译向我们倾诉:“以前在外面看病,找哪个科室检查都找不到,通过写字也有很多东西没法沟通。这里有义工老师带我们去,很方便,心里感到很安慰。”
看病难,是聋人面临的普遍问题。看病涉及到很多专业用语和细微感受,稍有差错,就可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,这也给手语翻译增加了难度。
“比如说疼痛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。”边海桢一边介绍一边比划着,“神经痛就是像橡皮筋一样有弹性的痛。刺激痛就是像针刺一样痛。还有一种是麻痛,像雷电一样,麻痛。痛的类型不一样,病情可能有很大差别。”
每次助聋门诊,都配备手语翻译3名,可聋人患者往往会有好几十名。整个下午,边海桢甚至没时间停下来喝口水。常常有好几名患者同时对他打着手语,让他应接不暇。
边海桢自己也出身于聋人家庭,父母都是聋人,只能靠手语和他们兄弟姐妹交流。这样的家庭环境,让边海桢从小就深知聋人的各种不易。
“你只要帮到他一点点,他会十分信任你。说夸张一点,他会依赖你。”边海桢说,“比如我帮聋人看病,他各种事情,家里的事情,朋友的事情,或者不能解决的事情,他都会找你求助。”
医院的助聋门诊开始于年,它是全国第一个助聋门诊,由医院和上海市聋人协会共同举办。时间固定在每周五下午,5年来已经服务了人次。
医院社工部主任吴晓慧介绍,之所以会开设助聋门诊,和五年前的一次义诊有关。“那次的聋人义诊,偌大的一个门诊大厅,只看到两百多人在里面,没有声音,只是手指在舞动。”吴晓慧说,“那一刹那我们医护人员是很震撼的,我们感到这群人看病是很辛苦的。医院领导决定用我们的方式,为他们做些什么。”
服务员不耐烦了,我很尴尬早晨,热闹喧嚣的菜市场,叫卖声此起彼伏。徐金妹也夹杂在买菜的人群中,衣着入时,打扮干净整洁。可她面对的,却是一个静音的世界。
称好重量之后,摊主报了价格。徐金妹专注地盯着摊主说话的口型,试图从中读出他在说什么,可看了半天,仍是一脸茫然。尴尬的场面持续了几分钟,摊主灵机一动,拿出笔和纸,把菜价写在上面,这才让徐金妹明白。
徐金妹是一名聋哑人,从出生那天起,她的世界就被按上了静音键。买菜购物之类的事,通过手势还可以勉强沟通。但遇上一些更复杂的问题,徐金妹往往束手无策。前些时,她和一名听力正常的同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。他们尝试着用纸和笔对话,试图把问题讲清楚。可最后双方还是无法相互理解,不欢而散。
这件事让徐金妹很苦恼,她向好朋友边海芳求助了。边海芳是边海桢的妹妹,也是一名手语翻译志愿者。
“我和他们双方沟通之后,发现矛盾原来是误会。”边海芳说,“经过我翻译之后,他们马上就握手了,没问题了。之前为什么有问题?还是缺少一个沟通。”
对于徐金妹的苦恼,出身聋人家庭的边海芳很能理解。徐金妹平时有什么苦恼,都会向边海芳倾诉。
“她去买衣服,服务员拿错第一件还可以,拿错第二件还可以,拿错第三件服务员就会皱眉,说烦死了,她很尴尬,好像没有办法表达。”边海芳说,“最后她很沮丧地离开了柜台,没有买到她所想要买的衣服。”
徐金妹夫妇俩都是聋哑人,让他们感到最庆幸的是,儿子的听力和语言能力完全正常。但徐金妹的儿子会的手语很有限,只能和她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。徐金妹平时接触最多的,还是聋人自己的小圈子。现在她经常用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gelishouhou.net/sjeldzl/8017.html
- 没有推荐文章
- 没有热点文章